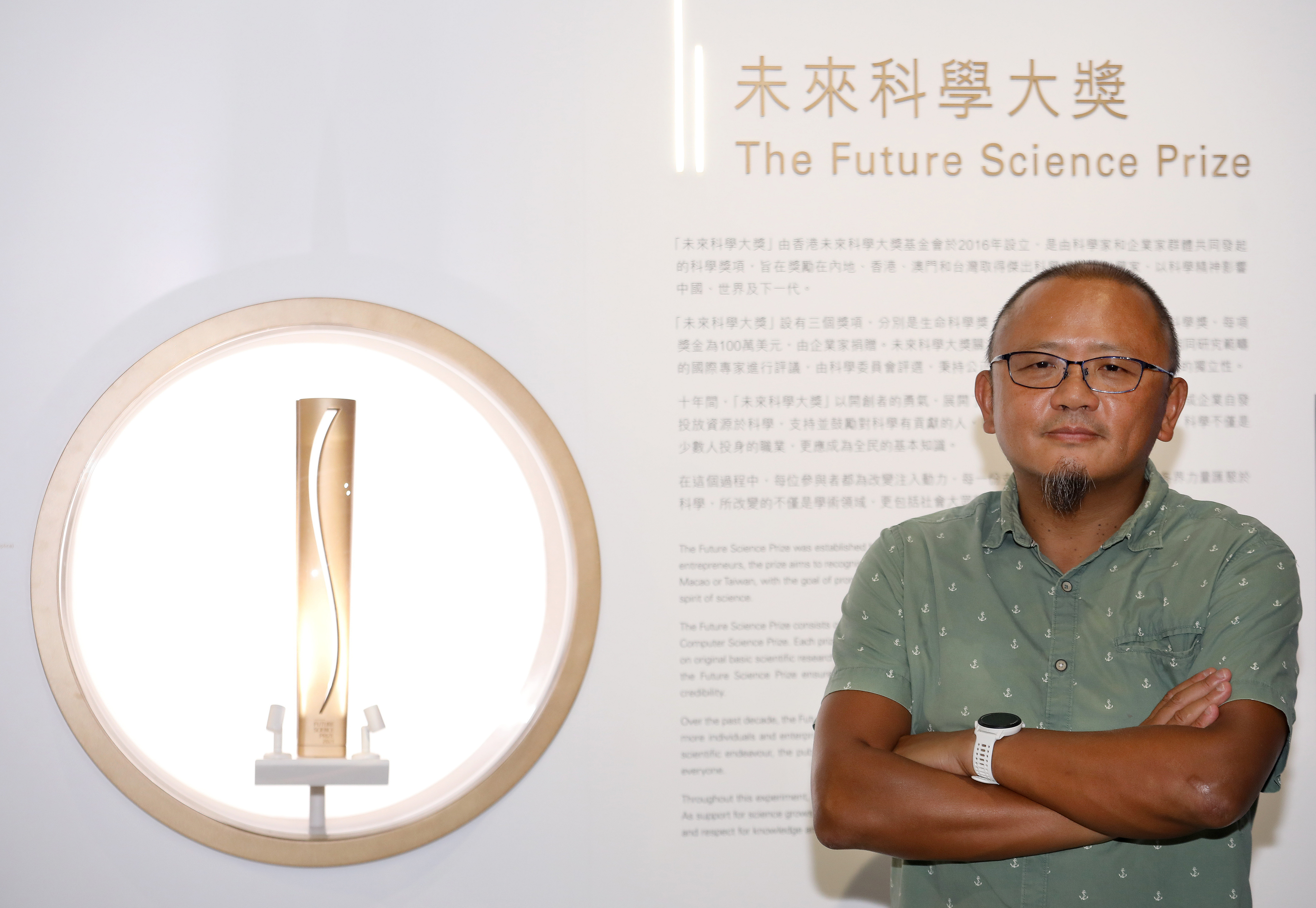【生命科学专场研讨会 - 塑造未来生物学】对话环节
主持嘉宾:
- 柴继杰,西湖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植物免疫学讲席教授,2023未来科学大奖-生命科学奖获奖者,未来科学大奖十周年庆典Program Committee委员
对话嘉宾:
- 管坤良,西湖大学讲席教授,未来科学大奖科学委员会委员
- 李家洋,崖州湾国家实验室主任,2018未来科学大奖-生命科学奖获奖者
- 李文辉,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清华大学生物医学交叉研究院教授,2022未来科学大奖-生命科学奖获奖者
- 刘勇军,华普生物科学创始人,小路生物创始人,未来科学大奖科学委员会委员(2018-2023)
- 卢煜明,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香港中文大学李嘉诚医学讲座教授,香港科学院院长,2016未来科学大奖-生命科学奖获奖者,2025未来科学大奖周Program Committee联席主席
- 施一公,西湖大学校长,2017未来科学大奖-生命科学奖获奖者
以下为对话全文梳理:
柴继杰(主持人):我们现在开始进入对话环节,刚才我们听了两个对话嘉宾的精彩报告,我首先第一个问题还是问管教授,他的研究我们刚才听了是关于肿瘤以及代谢。我想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肿瘤,肿瘤一直是医学领域的一个重大挑战,同时也是很多基础研究的一个重点方向。
我想请教管教授为我们展望一下,未来在肿瘤领域可能出现哪些突破性进展,同时为了加速这些突破性进展,我们应该重点关注哪些基础领域的研究方向?
管坤良:我本身不是医生,我是做基础研究的,做细胞生物学的。所以我说的观点有可能是片面的。但是我接着卢煜明教授的讲座继续下去,我觉得肿瘤的早期诊断在不久的将来会有重大的突破。卢教授已经展示过这方面的数据了,早期癌症病人的治愈率是很好的,晚期以后的治疗非常困难了。我认为早期诊断尤其随着技术的开发,分子水平的诊断,而不是根据肿瘤大小的影像诊断,比如在血液里面的肿瘤DNA的诊断,我想将来可能会有重大突破。
第二,过去20年在肿瘤治疗里面免疫治疗应该是最重大的进展,但不幸的是免疫治疗即使在好的情况下也只有40%左右的病人对免疫治疗有反应,比如说黑色素瘤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免疫治疗应该有重大的突破,从现在的单靶点、抗体,变成多靶点细胞治疗,抗体和细胞结合治疗也可能有很大的进展。
治疗的指标可能也应该有变化,从现在主要以延长生命为主要指标,将来可能会以改进生活的质量,功能性的治愈方面,我想在我有生之年,肿瘤可能是一个可以治疗的病,从致死的病可以变成像慢病一样的。
将来的研究:
第一,早期诊断方面我们需要更大的数据,更多的biomarker,而且每个肿瘤不一样的,更灵敏的,更可靠的模型来辅助我们的诊断。
第二,将来研究还是回到前面的肿瘤转移,肿瘤病人死亡的主要原因是肿瘤的转移,实际上肿瘤转移效率非常低,可能只有百万分之一的肿瘤细胞从原位能够离开,进入血液,再到别的组织能生存下来,那个地方对它是很不好的,很恶劣的,很难生存。因为我们身体里面免疫系统无时无刻不在杀死不对的细胞。但是你看现在的肿瘤研究,我们对肿瘤的发生有很多知识,两三百个基因突变会引起肿瘤的发生。到现在为止我们还不清楚有没有专门和迁移有关的基因的突变。我想对得肿瘤迁移和早期诊断这方面的基础研究会对未来肿瘤治疗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柴继杰(主持人):非常感谢管教授的分享,接下来我想问李家洋教授一个问题,简要介绍一下李家洋教授,我跟李家洋教授是同行,李家洋教授是影响力最大的植物分子遗传学家之一,在植物发育、作物遗传等方面均做出了很多原创性的发现,同时他在引领中国植物学以及中国现代农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李家洋教授是分子模块设计育种理念最早提出者之一,实际这与现代的智能育种不谋而合。想请教一下李教授,相比传统的育种方式,智能育种在效率上有怎么样的优势?同时智能育种未来面临一些技术或者是应用层面上的挑战,希望您分享一下智能育种发展的方向。
李家洋:非常高兴参加今天的未来科学大奖十周年科学峰会,作为一位嘉宾,刚才听了两位教授的报告,报告的都是与人类或肿瘤相关的,但是我们做的是农作物,是一个非常不同的领域。一个农作物是生长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不能动,也就意味着环境对它的影响非常大。比如说当地的温度、病虫害、光照都影响它的生长发育,这些都影响一个作物的产量和品质。
从育种学角度来说,我们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就在驯化野生的物种。现在,我们育种以前是传统育种,传统育种是遗传学建立之后以杂交为主的,这个过程主要是靠经验,所谓育种学家在过去又是艺术家,他通过他的观察想象与运气,能够培育出优良的品种出来。这样做主要是依靠经验,比较慢。过去就是主要依靠杂交育种,比如袁隆平先生,他也是2018年的未来科学大奖获奖者之一。
要培育一个新的品种,从杂交开始,全过程通常需要8-10年,这是运气比较好的。有的十年、二十年都做不成。但是现代科学的发展,特别是基因组技术取得突破以后,我2005年在国际上做报告的时候提出作物分子设计的概念,随着全基因组关联分析技术和基因克隆技术的应用,基因就容易找到,找到以后就把各种各样好的基因聚合起来培育一个优异新的好品种。
这里的问题就是找到基因以后在不同环境下它有什么样的表现?同样的种子放在东北种,跟放在江浙种,放在广东种表现完全不一样。智能育种应运而生。目前杂交育种和分子设计育种,都已经比较成熟了,但20年前提出的时候,大家基本上认为设计育种很难做到或者不可能做到,当然后来发展非常快,现在作物育种基本上都在用分子设计育种。
现在提出的智能育种,指的是智能品种智能制造,简称智能品种智造。这里有三个问题要解决:第一怎么把控制农作物重要性状的基因网络解析清楚,比如说产量、品质等;第二,同样基因型在不同地区表现怎么样?就是基因型和环境的关系,未来如何把环境与基因型之间的关系解析、适配、重构完成。我认为这是未来最大的一个挑战,未来智能育种可以把原来8-10年才能出来一个品种,做到3-5年。它的挑战就是:第一,精准构建一个环境与基因相互作用的数据库,并且让大家能用;第二,阐释清楚各种各样的农作物性状的基因、网络是怎么调控的,跟环境是什么样的关系、如何适配;第三通过人工智能,通过大数据,通过生物技术创造出一个生物决策体系出来,实现更高水平的适配,这样我们就能够快速培育出产量高、品质又好,又稳产的超级品种。
柴继杰(主持人):非常感谢李教授关于智能育种的精彩分享。
接下来想问李文辉教授一个问题,文辉教授我跟他非常熟悉,他是著名的病毒学家,在乙肝和丁肝研究方面有很多原创性的工作,尤其是发现乙肝病毒受体,为开发新型乙肝制药物质提供了关键靶点,他也因此获得了2024年乙肝研究杰出成就奖。实际新冠以后,我想每个人,不仅生物学的人,以及所有的大人、小孩对病毒非常熟悉。想问一下您认为病毒学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您对未来病理学的研究有何期待?
李文辉:病毒学是历史较长的学科,也是综合性很强的学科。病毒是在细胞内复制,但是可以在细胞间传播,也可以在个体内传播,在群体内传播,甚至在不同的种系之间传播。病毒学的发展受益于基础科学的进展,反过来病毒学的进展也带动了相关领域的发展。
在我看来,在可见的未来,病毒学的挑战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来看。从宏观层次来看要预防急性大规模的病毒性传染病。微观层面来看就是要对病毒学的机制有更多的了解,对于我们生命本身有更多的了解。对于这些挑战的重点我想从大的方面,宏观上来看就是急性传染病,这些急性传染病给人类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对于它的重点应该在于预防,如何不断地完善公共卫生体系,充分收集、分析以及利用相关的大数据,帮助我们能够有效应对未来的传染病,病毒性流行病,以及同样重要的是,如何更好研发和储备共性的研究系统和技术平台。
对于挑战难点来说,我的理解是如何能够治疗和消除慢性病毒性感染的危害。这里首先包括大家都比较熟知的乙型肝炎、艾滋病, EBV的感染等等。这些病毒可能可以被控制,很难被消除。也包括其他的疾病,慢慢大家有新的发现,如单纯疱疹病毒,不仅可以造成反复发作的疱疹,也有一些线索可能提示它和神经退行性疾病有关。
应对这些所谓能够潜伏,在一定条件下能够激活的病毒是一个科学界很大的难点。随着科学的发展,在分子生物学和细胞生物学基础上综合运用生物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定量生物学和其他的生物学概念、技术和方法通过深入回答一些基本的生物学问题,比如病毒在细胞里面到底在哪?如何潜伏的,如何被激活的?这些问题可以为解决上面这些挑战提供一些新的机遇。
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准确地定量,建立数学模型,逐渐的做到可以预测,这是将来我们期待的一个方向,在这一过程中运用人工智能进行有效的数据分析,以及应用AI进行相应的药物设计,前景十分广阔。
我个人的期待,未来可以及时识别,并且有效控制,通过公共卫生措施和疫苗等手段宏观上控制病毒传染病的危害。微观层面慢性感染性疾病里面,基本的生物学机制上希望有新的研究突破,产生像抗生素一样的广谱的抗病毒药物。目前稍微广谱的抗病毒药物只有干扰素,但副作用大、机制复杂,期待未来通过深入研究能够发现新的机制,能够有效、广谱地应对病毒的感染。
在我们自己的研究领域里头,最严重的病毒性肝炎就是乙型肝炎合并丁型肝炎,全球大概1200万人感染了丁肝,未来这些病人可能可以用药物治好。对于乙肝来说疫苗的效果很好,我们国家预防工作做得很好,但是全球有超过2亿人感染慢性乙肝。目前的药物只能控制,可能新的一些研发药物里面联合使用也只能在部分人群中实现临床治愈。我们期待并相信在基础研究方面有更多的发现,尤其在病毒在细胞核内储存池机制的理解和病毒DNA的转录的控制方面有所突破,这些会带来新的治疗靶点和治疗范式的变革。在更为长远的未来希望病毒性感染性疾病不再是人类的一大困扰,谢谢大家!
柴继杰(主持人):谢谢文辉教授既专业又通俗关于病毒方面的分享,接下来想问一下刘勇军博士,刘勇军博士可以说是跨学科的专家,因为他既是国际出名的免疫学专家,同时可以说在产业方面取得非常卓越的成就,目前是小路生物公司的创始人,不止一家公司,同时也是免疫治疗转化的先锋之一。想请教一下刘勇军博士,你如何看待当前生物医学领域中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想分享一下我们应该如何更好地推动两者之间的融合?
刘勇军: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historically实际上是基础科学在先,应用科学在后,应用这个原理到药物的研发和改善人类的健康,基本上都是这个关系。但是,基础科学研究的topic是有时代性的。
现在,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同时,两者是非常互补的,我是学免疫的,在这里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关于免疫学的基础科学和应用学的关系,免疫学实际上有100多年的历史,人类在抗病毒感染、抗细菌感染、抗瘟疫过程中,意识到人体内有一个免疫系统,这一百多年来免疫学基础科学所要解决的2大问题:
1. 免疫系统由什么组成的?我们知道我们有胸腺,有骨髓,产生十几种免疫细胞,它们去了淋巴结、肠道,这是我们免疫系统,免疫系统如何工作的?像物理学的力学一样,我们免疫学也有定律,免疫学的第一定律就是免疫学有diversity,免疫系统可以对世界上任何一个病毒细菌都可以反应,同时它可以对于人工制造的物质也产生反应,diversity基本上是unlimited,解决免疫系统diversity,世界上最少出了两个诺贝尔奖。
2.免疫系统的专一性,它一旦识别一个病毒只识别这个病毒,不识别其他的东西。因为这个原理我们产生了单克隆抗体,一个单克隆抗体是由一个B细胞产生的,你把它克隆了,就变成了一个单克隆抗体,现在在我们的药物界,好像差不多有一半左右最有价值的药都是和单克隆抗体有关系。免疫系统还有两个定律,一个定律是免疫有记忆。所以我们在做抗感染、抗肿瘤的时候最好把免疫记忆最大激活,免疫系统还有一个定律,英文叫nonself、discrimination,就是免疫系统有一些受体,我们柴老师对这个有重大的贡献,它只识别病毒和细菌的一些shared structure,它不是别自己。所以这些原理的应用,我们实际上最少有30多个非常大的药,transformative medicine都是从这里translate出来的。比如说单克隆抗体,修美乐是一个药王,这20年世界上最大的药就是修美乐,现在出现了PD-1,我们现在出现了抗过敏的,差不多十几种过敏性疾病这个药都很有效。我们一公的公司、王晓东的公司都在阻断一个受体叫BTK,它既可以治肿瘤,又可以治自身免疫病,所以我们免疫学在基础科学和转化医学,实际上是非常productive field。但是我们对于免疫系统的认知非常有限,主要反映在我们对很多疾病的无奈。比如说慢性病毒感染,我们的肿瘤免疫治疗,基本上是20%有效,我们开发的最先进的抗过敏性疾病的新药也只有50%有效,另外有很多疾病,一停药就复发,这说明我们对于免疫系统最基本的机制上面还有很多不知道的东西。要想知道这些基理,实际上我们要先从应用上入手,再从解决难题上入手,来发现新的机制。
所以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是联系得非常紧密,区别在变小。是互相互补的。
柴继杰(主持人):非常感谢刘博士关于基础与应用研究之间关系的精彩分享。接下来我想请问卢煜明教授,刚才卢煜明教授已经分享了他令人激动的发现,这些发现不仅在基础研究上有深远的影响,同时卢教授在临床转化医学方面也取得了巨大成功。想请问卢教授,您作为生命医学领域的权威专家,如何看待未来基础医学领域和临床转化医学之间协同发展,我们应该让这两者之间可以更加有效地协同发展?
卢煜明: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效应,问题是两方面人才的培养其实是很不同的,比如说我记得当我是初级医生的时候,在医院里面通常要follow clinical protocol,就是有些人给你做了一个trial是什么样子,你就跟着,或者是有一些专业团体,你就跟他们guidelines,同一个PhD做研究的心态很不同,因此我想最重要是这两个领域,中间这条桥梁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全世界,有一些医生、科学家,physician scientist全世界这方面人才也是不够的,因此未来中国应该在这方面训练多一些这些人。比如说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每年有300个医学生进来,其中进来最好的15%我们会给他一个特别训练,他会选择在Year one开始去一个实验室工作,想他们在训练的过程里边在科学文化、医学文化同一时间学习。
在毕业以后,我们应该有一些特别的Program给他们一个可以同时兼顾clinical 和research两方面的机会,比如说我们有一些clinical lecturer的post,他们可以在没考试的时候,70%是clinical,30%是做研究,所以我想这也很重要,当然还有一些grant等等也同等重要,我知道施一公跟我也是在这个新技术系统里面,我想我们也希望用这些方面支持clinician scientist发展。
柴继杰(主持人):非常感谢卢教授关于基础研究临床转化医学之间的分享,尤其是从人才培养以及职业选择方面给我们很好的诠释。接下来想问一下施教授,施一公教授是著名的生物物理学学家,在结构生物学和细胞生物学都取得了世界级的科研成果,可以说为人类重大疾病治疗开辟了新的方向提供新的思路,同时他为中国科研体系与高等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我的问题是关于AI,AlphaFold,关于蛋白结构预测以及David Baker蛋白质设计都极大推动了结构生物学乃至整个生物学的发展,实际Google在最近又推出了Aplhazero,可以进一步将AI技术延伸到基因组学甚至系统生物学,所以想问施教授,您认为这些AI的技术如何塑造未来生物学的研究模式?我们在哪些方面应该做出怎样的战略部署和前瞻布局?
施一公:其实AI确实发展特别快,深入到课堂、深入到研究一线,实际最底层逻辑永远不会变,在座每一个学生,包括我本人,最终你有批判性的思维,有好的基础研究的训练,你总是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但是具体怎么做呢?我觉得作为一个本科生、博士生还是要打好基础,还是要学会最基本的科学逻辑、批判性思维。社会包括很多学生误以为我们是以做结构谋生,绝不是如此,实际上是科学问题引导,结构是一个出口,在我实验室主要是生物化学和生物物理,我的实验室在十几年之前就完全转型不再聚焦于单个蛋白或两个蛋白,还是科学问题导引,什么样的科学问题你认为将来当单个蛋白,更多蛋白被AplhaFold被预测之后你需要解决生物化学的角度是你做事情的方式。
你能做什么呢?还有一个词叫科学研究范式的改变。在座每一个学生,不管做任何的博士课题,或多或少会和蛋白相连,把蛋白的同源结构做一个预测,或者蛋白本身做一个预测,去搜寻AplhaFold的data base,你会发现有几万个,甚至几十万个同源结构,实际上你用同源结构预测出来以后,你把基因序列和蛋白序列相似度最差的,不是最好的,最差的那些蛋白和基因拿过来做一个比较,你会脑洞大开,发现不同物种中保守的信号转导的通路,以前完全不为人类所知。
举这个例子告诉你,告诉大家我的思考,蛋白结构的预测AplhaFold使得我们可以把整个生物学的研究从遗传学到细胞生物学到生物化学到生物物理这个顺序打乱,你可以从生物物理出发,甚至三维结构出发,你可以倒推生物学功能,发现新的细胞生物学现象,新的疾病发生的机理,新的遗传学的规律,这在以前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因为AI的出现,因为AplhaFold的出现可以完全这样做。确实是颠覆了以前从粗到细,从远到近的研究方式,可以从近辐射到远方看得非常远,把人类的想象,对科学的追求延展的几个数量级。
继杰还问我政府应该怎么做规划?我觉得更多来自于自下而上的合作,学生彼此之间多合作,PI博士生导师多合作,跨学科多合作,打开思维,让AI在过程当中辅助我们,AI可以帮助我们想得更好。哪怕几年大家还一直在debate AI有没有自由意志,我觉得这个问题好像大家不太讨论了,因为所有的自由意志都是过去基于过去的经验,过去的总结,过去的场景,已经可以总结,可以延展,可以给你新的主意,我觉得我们可以更好的用AI走得更远一点。
柴继杰(主持人):非常感谢施教授的精彩分享。AI非常有用,但是对于在校大学生而言,需要基础知识,培养好逻辑思维能力非常重要。
再次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分享,今天的生命科学专场到此结束,谢谢在场各位嘉宾。
相关阅读: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煜明教授《创造分子诊断领域范式转变》|未来科学大奖十周年庆典·科学峰会